我今年五月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成绩中等,在校园里不算出类拔萃也不算默默无闻。我从入学到毕业之间运气非常好,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我得到了保持了四年的友谊。另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我在大一拿到了喜欢的行业里最好的实习机会,使我一直没有找工作的压力。另一系列在其他学校难得的机会让我大学四年学业充实但不繁琐(当然这是现在这么想的,当时还是很头疼的)。
但我这个答案不会写我怎么度过这四年的。我的故事太平淡了。我在这里写一下我三个很有趣的朋友的故事。这三个朋友在自己的路上走得比同龄人都远很多很多。我就叫他们C,E,和G吧。
▌阿C
刚入学时,我很吃惊地发现有那么多同学其实已经互相认识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很多都是从同一个寄宿学校/超级高中认识的。但有一个长相不怎么起眼的C同学,则是其他同学主动相见介绍自己的。所有人的开场白都是“啊,你一定是C,我听说过你”。只有我不认识他。
这个C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我说的不是“考试得满分”的天才,而是“16岁时有街边卖的杂志介绍他的计算机天赋”的天才。
也许C注意到我是他楼层唯一一个华裔男生,在搬进宿舍的第一天晚上他就过来自我介绍,在得知我想学数学后,C就不留余力推荐我上大一最难的数学课,Math 55。这是一门传奇的课程,据说一年内可以学完大学四年的数学课。教课的是26岁拿tenure的传奇教授Noam Elkies。后来事实证明我上完这么课以后的确是上完了四年的数学课——被折磨过后再也不想碰纯数学了。
我和C在Math 55不算好学生。每周的problem set只有10道题,但每道我们都不怎么会做。这门课允许学生一起做作业,我和C每周就和班里几个比较好的学生一起做作业,希望他们能“辅导”我们。 就这样,我这个数学一般的学生莫名其妙地认识了同届数学最好的几个同学,包括另一个学术成绩被媒体报道过的D和Math 55全班认为天赋最高的G同学。后来大二分宿舍时我和C和D选择住在一起,友情延续了四年。
大一过了一半的时候C突然跟我说他想暑假去金融公司实习。他满怀希望地申请了行业里名声很大的J公司,并邀我陪他一起训练J公司喜欢问的速算数学题。和他一起训练速算题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件事——C在面试中表现不佳没有拿到实习,而我拿到了。C最后选择去了另一家金融界内名声很大的公司,而他被录取是因为这个公司的核心职员曾经在杂志上读过C的生平。
但C在实习以后跟我说他并不喜欢金融,而更喜欢跟着他认识的几个计算机前辈去创业。他在学校一个招聘会上认识了他一直崇拜的Adam D'Angelo,就是Quora的创始人。Adam也是从高中起做编程竞赛的天才,毕业后进了到时还是中型创业公司的Facebook,当上Facebook CTO以后退出公司跟Charlie Cheever一起创业。C因为背景和Adam太像,视Adam为开拓路线的前辈+偶像,在Adam邀请下大二结束后到Quora实习。Adam后来建议C假如他想自己创业,毕业后应该到比Quora更小一点的公司。
C因为这个建议大三时休学了一个学期,专职在Quora工作,顺便在旧金山找小型创业公司。这段时间我因为忙,很少和C联系。C休学后回到学校,给我感觉成熟了很多。他在哈佛的最后1.5年完全不把学业放在眼里。以前Math 55时我们愿意连续熬夜为了完成一个Problem set,而C从Quora回来后学会了专门挑简单的课。就算这样也经常不去上课,有次因为想去South by Southwest不请假直接连续翘课10天。C在旧金山发现了fame比聪明更重要,开始学习如何让自己/自己的产品迅速传播出去,尽管这和C的专长截然不同。他还发现了哈佛人际交往的重要性,经常通过这种hackathon和交流会认识更多的人。这和他大一时在宿舍里锁着门不跟客厅里的人玩真心话大冒险截然不同。
C也开始关注自己外部形象和女生了。这段时间我听C讲的最多的就是怎样调节饮食和健身。我在他的“威压”下开始和C一起健身。我们还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深夜讨论女生。很让我惊讶的是,C在和女生交往方面有着天生的自卑。这也许和他作为亚裔男生在美国长大的背景有关。他在这段时间里尝试和很多女生交往,去了很多次date,也用tinder“钩”到一些女生。但他总觉得那些女生和他不在一个“节奏”上,没有趣味。我开玩笑说假如我是女生你应该会喜欢上我,他说假如有更多女生像你一样就好了。
C在毕业前夕(真的是领毕业证书前一晚)终于和他四年的红颜hook up了。现在两人不知道是否还联系。C毕业后去了一家startup,还没报到startup就被收购了,他的股权应该增长了很多。在硅谷这个什么事情都可以瞬间改变的地方,C也许很快会变得让我认不出来。在他兑现股权以后,我相信他身边会有很多他学生时代接触不到的“有趣味”的女生。届时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深夜像我表白。
▌阿E:
阿E的故事其实是两个人,阿A和阿E的故事。两人都是土耳其人,两人政治热情都很高,但两人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阿A是参与过广场革命的左翼反对派,而阿E的爸爸是土耳其总统(不是Erdogan是Gul)。
阿A认真来说并没有在哈佛度过“本科四年”。他是大二转进来的插班生,因为学校宿舍不够用就插到我朋友宿舍里了。他跟我朋友当室友一年内关系不错,第二年就搬来和我,我朋友,还有其他7个人一起住大公寓。
阿A身材微胖,有一张大圆脸,一看就是性格很平和的人。平时在宿舍里以和为重,很多纠纷都是他来圆场的。宿舍里打扫卫生这类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活一般也是他来完成。但他温和性格的背后则是他激进的政治主张。他在高中时期就加入了土耳其某个左翼反对派政党的青年部,在大学期间仍经常写政治类文章发表在该党青年报。他憎恨土耳其当时的总理(现在当总统了)的Erdogan,认为Erdogan将把土耳其带成比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更极端的非世俗国家。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介绍一下土耳其政治和Erdogan(这都是我记得的阿A和阿E讲的部分,有错是我记忆不好)。Erdogan是个极有个人魅力的宗教主义者。他在九十年代当伊斯坦布尔市长时体现了他的执政能力。但他和他的政党在九十年代被当权者打压,Erdogan也因为在广场上宣读宗教诗歌入狱。但由于葛兰宗教运动和萧条的经济,Erdogan带领的AKP于2002年得权,Erdogan成为土耳其总理。在他当总理前,土耳其经济崩溃。他在上任前几年控制了资金外流和通货膨胀。他加速了土耳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跟欧洲和中国贸易稳健上涨。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也迅速上升。Erdogan的个人魅力和政绩让他连续高票连任,他也因为民众的支持,得以推进他的权力控制——他支持政教合一,并努力打压历史上更世俗化的军队和法院系统。
在我看来,他的当权,集权,和改革的手段相当高明,对土耳其的贡献不亚于邓公对中国的贡献。但阿A认为他藐视宪法和威权的手段是他不可原谅的污点。阿A坚信他必须为Taksim广场镇压学生而辞职。阿A的很多好友在Taksim广场示威,阿A也考虑过休学几个月去广场支持他们。在那段时间,跟阿A聊天他只有土耳其和Erdogan这一个话题。他跟我说现在是土耳其国运的转折点,要是他早知道是这个样子,他应该会留在土耳其而不是来哈佛留学。
阿A最后还是回土耳其两次,好像两次都是为了在选举中投票。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的机票钱可以贿赂到100张选票,他说我回去投票就是为了让买选票这样的事不会在土耳其发生。
我很欣赏阿A的政治热情和勇气,但我总觉得他和我对政治的兴趣点很不一样。阿A能看到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并为其受害者伸张正义。但我很难和他沟通抽象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比如说,他能很敏锐的觉察到土耳其的经济不平等如何增加了宗教力量,但我问他不平等是否是必然现象时,他却对这个问题不怎么关心。他很热心建立一个”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但对这个alternative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并不关心。我相信阿A比其他人思考政治问题更多,但我不确定他比其他人想得更深刻。
比起阿A来,阿E的思考和关注点和我更接近。我们两人连续上了两门哈佛很难进的历史学二十人的seminar(讨论课)。第一门是Emma Rothschild的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第二门是Niall Ferguson的International Finance。在这两门课里,我们两个都是占少数的经济右翼,也是少数的国际学生。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美国顶尖学校的讨论课上,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竟然是两个外国人。我们的背景和立场让上课讨论非常有趣,经常是美国学生提出观点(尤其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后老师转向我们问“真的是这样的吗”,然后等我们的一系列反驳。
其实“一系列反驳”主要来自于我,因为阿E的英语让他无法在课上当场进行辩论,但他说话时观点还是很有趣的。Ferguson给我们的读物中有一篇认为伊斯兰国家近代的衰落源自于伊斯兰教对现代商业的排斥。阿E就拿了同期欧洲各国的宗教政策横向比较,表示奥斯曼帝国(就是土耳其的前身)比同期欧洲国家商业气氛更好。他认为英国(经济)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并不是法兰西或者普鲁士的absolutism,而是奥斯曼帝国的政军教三权合一。
这些观念在我听来,不明真假,因为很像土耳其爱国教育的产物。但阿E把我真正雷到的,是他在Niall Ferguson的课写的论文,该论文题为:
新奥斯曼帝国:如何在中东建立以土耳其为中心的经济共同体(阿E你这么大野心你爸爸知道吗)
(这论文当然很难写,但我觉得他说的的确很有道理。中东几千年以来最和平的时期就是奥斯曼大一统时期。那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都能在帝国统治下生存。也许中东的未来的确需要一个强大的,宗教化的经济领头羊。)
阿E和阿A关系很好,虽然阿A认为阿E的父亲应该入狱。在我眼里,阿A和阿E是为了一个目标——土耳其的民族复兴——努力。在土耳其人眼里,阿A和阿E是不共戴天的政治宿敌。因为他们的政治和我无关,我可以从远距离从他们身上看学生时期政治生活应该怎么过。在学生期间,政治是理想,是智力游戏,是找志同道合的人的渠道,但绝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在表达政治理想时没有必要人身攻击,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目标将对手抹黑或者让对方闭嘴。在这点上,这两个土耳其人比很多其他哈佛同学高明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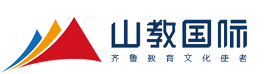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添加为好友)
(微信“扫一扫”添加为好友)